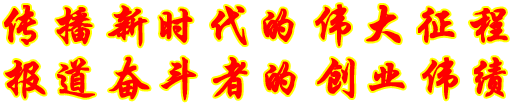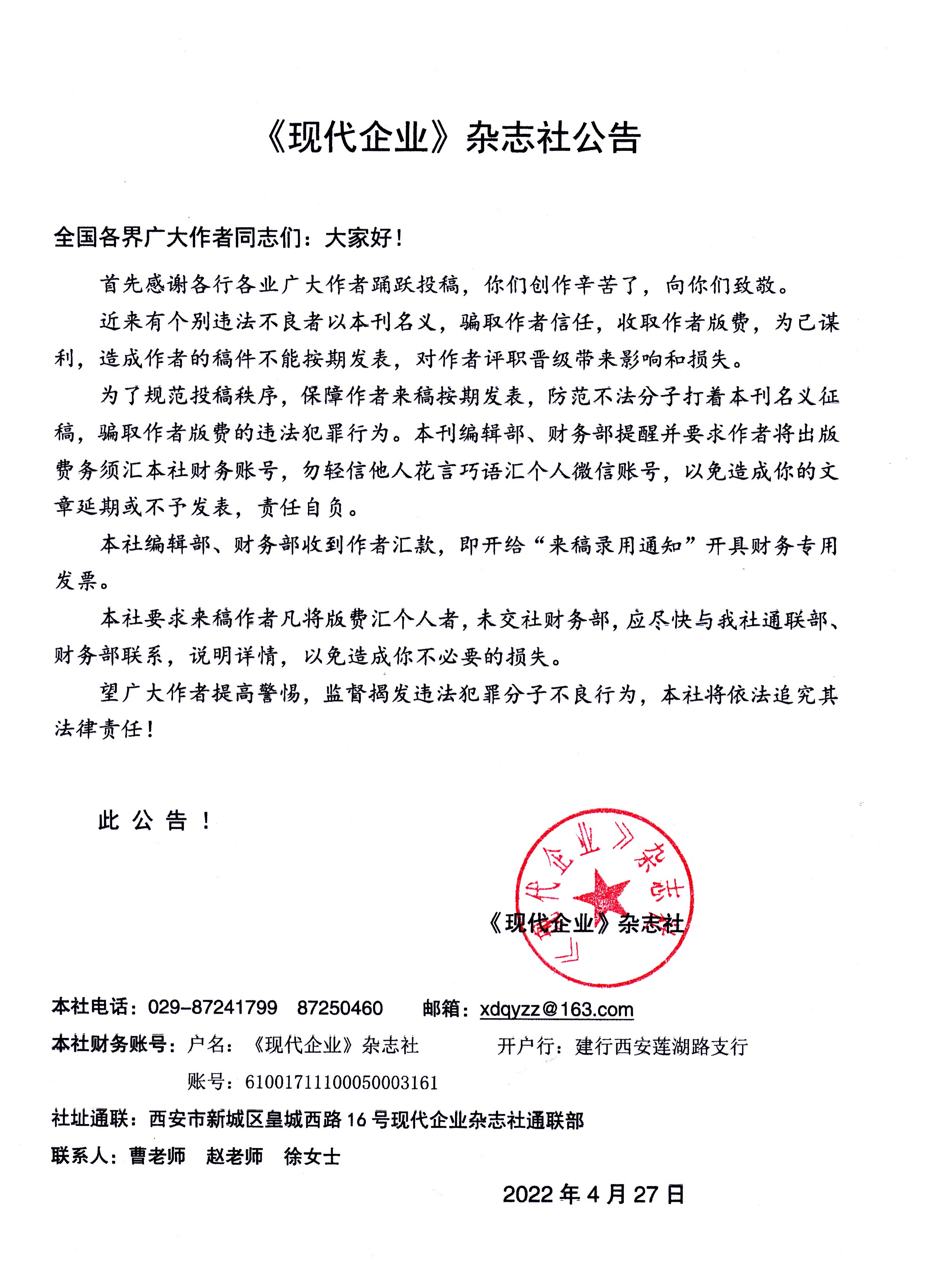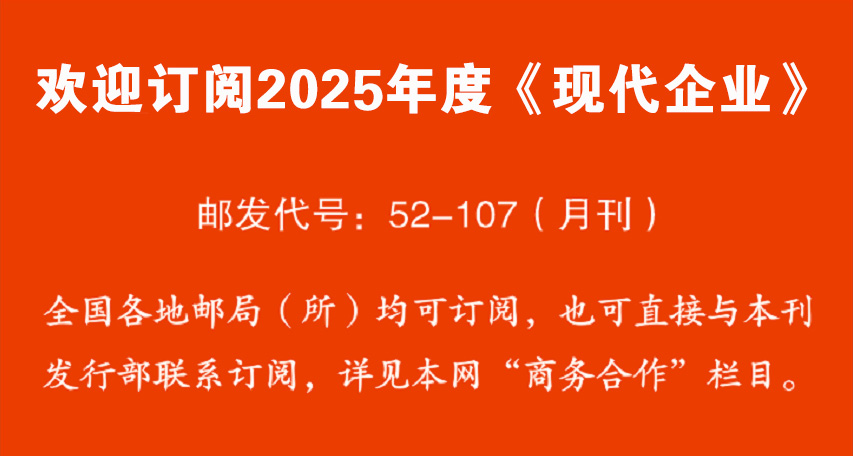為獻(xiàn)禮二十大、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與延安市融媒體中心再度攜手,特別推出廣播節(jié)目《獻(xiàn)禮二十大·永遠(yuǎn)跟黨走—— 黨的故事我來講(第二季)》,作為黨的追隨者、時(shí)代更迭的見證人,我們將繼續(xù)邀請(qǐng)多位為延安貢獻(xiàn)過青春與智慧的老干部走進(jìn)廣播直播間,講他們眼中時(shí)代的變化,社會(huì)的進(jìn)步。
本期嘉賓:賀彥清,男,中共黨員,曾任中共延長(zhǎng)縣委宣傳部副部長(zhǎng)、宣教黨委書記、宣傳部三級(jí)調(diào)研員,現(xiàn)為延長(zhǎng)縣延安精神研究會(huì)會(huì)長(zhǎng)。
輝煌的延長(zhǎng)石油及其第一位模范廠長(zhǎng)陳振夏——賀彥清輝煌的延長(zhǎng)石油及其第一位模范廠長(zhǎng) 陳振夏
石油,被稱為工業(yè)的“血液”。而延長(zhǎng)石油在中國(guó)石油史上又具有獨(dú)一無二的特殊地位。
據(jù)考古學(xué)家考證:中國(guó)是世界上最早發(fā)現(xiàn)和使用石油的國(guó)家。3000多年前周代《易經(jīng)》中就有“上火下澤”“澤中有火”的關(guān)于油氣火苗的記載。另?yè)?jù)《漢書·地理志》載,在今陜西延長(zhǎng)縣,水面上漂有可燃液體,人們“接取用之”。《后漢書》《水經(jīng)注》《元和郡縣志》等不同時(shí)期古籍都對(duì)先民們開發(fā)利用石油有所記述。石油在古代的用途已較為廣泛,有用于日常生活的,有用于書法繪畫的,也有用于醫(yī)療的,甚至還有用于軍事的。在宋朝以前,“石油”并不稱石油,而叫硫磺油、雄黃油、石瑙油、猛火油、火井油、泥油、石漆等,名稱較多。宋代科學(xué)家沈括所著《夢(mèng)溪筆談》稱,“鄜延境內(nèi)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現(xiàn)“石油”這個(gè)名字。這里的高奴縣即今延長(zhǎng)縣。近代以來的舊中國(guó),國(guó)家民族積貧積弱,無力大面積勘探開釆石油,我國(guó)被許多外國(guó)專家扣上“貧油”的帽子。好在,百余年前的1907年,在當(dāng)時(shí)的候補(bǔ)知縣洪寅等一批有識(shí)之士積極奔走努力下,在延長(zhǎng)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中國(guó)陸上第一口油井誕生了。百年風(fēng)云激蕩,百年鑄就輝煌。在數(shù)代延長(zhǎng)石油人的艱苦努力下,如今的延長(zhǎng)石油,已經(jīng)是馳名中外的大型企業(yè),名列世界500強(qiáng)。延長(zhǎng)也成為舉世聞名的石油故里,這里不僅是中國(guó)石油工業(yè)的發(fā)祥地,也是埋頭苦干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發(fā)源地,更是中國(guó)石油人的朝圣地。從小到大,由弱到強(qiáng),百余年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其經(jīng)過的道路并不平坦,而在這不平坦的道路上,延長(zhǎng)石油能走到今天的輝煌,是與一名老廠長(zhǎng)分不開的。他就是延長(zhǎng)石油廠第一位模范廠長(zhǎng)陳振夏。1938年2月,從上海輾轉(zhuǎn)到延安,受黨組織派遣,到延長(zhǎng)石油廠擔(dān)任技正和工程師,成為延長(zhǎng)石油廠生產(chǎn)負(fù)責(zé)人。當(dāng)時(shí)延長(zhǎng)石油廠共有職工50余名,日產(chǎn)原油只有100多公斤,幾乎處于停產(chǎn)狀態(tài)。要恢復(fù)和增加產(chǎn)量需要修復(fù)舊井或打新井,但是,當(dāng)時(shí)但這一切難不倒勤學(xué)善思、聰明智慧、吃苦耐勞、敢于創(chuàng)新的陳振夏!他不斷向老工人和當(dāng)?shù)厝罕妼W(xué)習(xí),到附近村莊搜集戰(zhàn)爭(zhēng)期間疏散在四處的設(shè)備器材,對(duì)廢舊設(shè)備進(jìn)行修復(fù),通過科學(xué)實(shí)驗(yàn)進(jìn)行技術(shù)改進(jìn),實(shí)在找不到的配件就自己打造或用木頭代替。為了把戰(zhàn)爭(zhēng)期間疏散在四處的設(shè)備器材情況搞清楚,陳振夏親自深入延長(zhǎng)至永坪沿途過去藏機(jī)器的各個(gè)村莊,訪問當(dāng)?shù)厝罕姡瑢⒉貦C(jī)器的窯洞逐個(gè)清理,造冊(cè)登記。他還撰寫了書面報(bào)告,提出用收回器材打新井的建議計(jì)劃。當(dāng)時(shí),打油井需要技術(shù),大家都沒有學(xué)過地質(zhì),怎么辦?廠里原有的地質(zhì)資料,早已遺失殆盡,更沒有測(cè)量?jī)x器。陳振夏到處搜集參考書,只找到一本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化學(xué)工業(yè)大全》,其中的石油卷,還是主要講石油提煉的。而怎么測(cè)量,怎么定井位,問題和困難一個(gè)接一個(gè)。但陳振夏沒有被困難嚇倒。他逐個(gè)詢問老工人,聽他們回憶相關(guān)往事。他跟著老工人,爬到延長(zhǎng)西山上,調(diào)查、尋找曾經(jīng)選定過的井位。幾經(jīng)調(diào)查,在延一井北面的半山坡上,選定了延19井位置。由于缺乏打井所需的各種鋼材,鉆井井架除了4根角柱用的是6英寸的鋼管外,其余部分,用的都是木結(jié)構(gòu)。蒸汽機(jī)底座、傳動(dòng)機(jī)構(gòu)的承力立柱和橫梁(可叫“油梁”),都是陳振夏帶領(lǐng)工人們到深山老林里砍伐原木并拉運(yùn)回來。最大的油梁約10米長(zhǎng),最大剖面須達(dá)到600×1000毫米,而且要求木質(zhì)必須結(jié)實(shí)。因?yàn)橐页叽缱銐虻脑荆麄冎缓脦е杉Z,拿著灶具,自己做飯,晚上住在野地里。陳振夏與工人們吃住在深山。有時(shí),幾天幾夜回不來。至1940年春,陳振夏帶領(lǐng)大家硬是靠東拼西湊、人拉肩扛、自修自造一舉在延長(zhǎng)西灘洼半山坡上鉆成延19井,初日產(chǎn)量竟達(dá)到1.6噸!徹底扭轉(zhuǎn)了被動(dòng)局面,大家親切地稱這口井為“起家井”。他總是想法設(shè)法做到物盡其用。每一顆螺絲釘,每一段鋼絲繩在他那里都是打井的“瑰寶”。當(dāng)時(shí),只有兩部標(biāo)準(zhǔn)頓鉆,兩套打井動(dòng)力。陳振夏帶領(lǐng)工人師傅認(rèn)真操作,精心維護(hù),生怕?lián)p壞任何一個(gè)零部件。鉆頭刃口打鈍了,鋼了又鋼。管鉗的牙齒磨光了,銼了又銼。鋼絲繩,只有200多米的一根比較新,其中還有不少松綻或斷股,銹蝕不堪。陳振夏和工人師傅們,利用工余時(shí)間,細(xì)心地將每一根斷、壞鋼絲剔除或剁掉,把新的重新擰鉸起來使用。他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工人們說“這200米鋼絲繩,可是我們打井的生命線呵!要像愛護(hù)自己的眼珠子一樣愛護(hù)它。”他常常通過技術(shù)改造,變被動(dòng)為主動(dòng)。在煉油廠期間,沿用原來的大小兩套老式單獨(dú)釜煉油。裝鍋、燒火、出油、分蠟,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為了解決燃料問題,陳振夏帶領(lǐng)工人上山砍柴,開荒種地,這樣在解決燃料問題的同時(shí),也解決了糧食問題。他還用單獨(dú)釜里清理出來的鍋巴、油土,摻上碳沫制造混合燃料。一鍋這樣的燃料,可抵石炭225公斤。為了加快煉油速度,陳振夏在煉油釜里鉆出鉆進(jìn),反復(fù)研究,改敞口小火脫水為加蓋大火脫水,每煉一鍋油可縮短2小時(shí)左右。為解決材料問題,陳振夏想盡了辦法。用石灰代替石棉,用動(dòng)物骨灰代替硫酸,用玻璃屑代替汽門砂。因七1井、七3井打出旺油,加工設(shè)備明顯不夠用,陳振夏帶領(lǐng)職工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取出美國(guó)人在延長(zhǎng)打井時(shí)下在井里的20多根12英寸的套管,經(jīng)破開展平,鉚制了4口煉油鍋、1臺(tái)蒸汽鍋爐,不但解決了原油加工設(shè)備不足的問題,還順便增加了打井設(shè)備。月煉油量達(dá)到15000小桶,比原來每月2700小桶增加了5—6倍。他經(jīng)常自加壓力,不斷擴(kuò)大再生產(chǎn)。在努力提高煉油量的同時(shí),陳振夏還在增加成品油種類方面下功夫。他從實(shí)際出發(fā),與工務(wù)科長(zhǎng)顧光研究生產(chǎn)黃油。他們以重油為原料,經(jīng)過10多次試驗(yàn),終于試制成功,投入生產(chǎn)。這一新產(chǎn)品的誕生,使陜甘寧邊區(qū)各種機(jī)器所需要的潤(rùn)滑油,開始自給。更可貴的是能變廢為寶,掌握用油渣提煉油墨的技術(shù)。1943年冬天,職工用浸濕的32條毛巾,撲滅了煉油部土油池的一場(chǎng)大火,也是用土辦法代替消防器材的生動(dòng)例子。他既善于動(dòng)腦,也勤于動(dòng)手。在技術(shù)力量相當(dāng)薄弱的條件下,石油廠設(shè)備卻在陳振夏領(lǐng)導(dǎo)下,不斷擴(kuò)充。從只有一盤烘爐開始,逐漸充實(shí)到擁有了6尺8車床兩臺(tái),手搖鉆、手板刨各1臺(tái),小化鐵爐1座,烘爐2盤。為了克服設(shè)備和原料匱乏的困難,陳振夏想了很多土辦法。一次,鉆桿絲扣壞了,車床太短,無法維修。陳振夏與技術(shù)工人劉國(guó)威干脆把兩部車床接起來使用,把鉆桿絲扣車好。又一次鉆機(jī)大軸斷了,為了不延誤鉆井工期,陳振夏與鍛工一起,硬是在烘爐里鍛造,運(yùn)用公母榫原理,加以修復(fù)。烘爐里溫度非常高,他們的衣服都濕透了,汗水順著臉頰一直流淌。在高溫烘爐的炙烤下,汗水變成了蒸汽,眼前一片模糊。無奈,他們就輪流著大干,直到大軸鍛造好為止。延長(zhǎng)人素來崇拜牛,以牛為精神圖騰,稱有本事能干成事的人為“牛人”。陳振夏就是這樣苦干實(shí)干的“牛人”!1941年12月,陳振夏被正式任命為廠長(zhǎng),廠里職工也發(fā)展到上百人,并且修建了石窯、工房、制蠟冰窖等,成立了修理部,修配機(jī)器、研制鍋爐和煉油鍋。還自辦了小煤窯!1943年,七1井、七3井先后噴油,當(dāng)年原油產(chǎn)量達(dá)到1279噸。陳振夏設(shè)計(jì)改造土法煉油,生產(chǎn)了大量汽油、煤油,提煉出了潤(rùn)滑油和黃油等,保證了黨中央和邊區(qū)政府、部隊(duì)和人民的生活用油,而且印刷油墨、軍工用油,燃料、洋蠟都得到充足供應(yīng)。延長(zhǎng)石油成為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要經(jīng)濟(jì)支柱之一,有民謠稱“延長(zhǎng)石油點(diǎn)亮了棗園的煤油燈,棗園的煤油燈照亮了中國(guó)革命的航程。”延長(zhǎng)石油廠贏得了“功臣油礦”的美稱。廠長(zhǎng)陳振夏的名字也傳遍了延安,傳遍了邊區(qū)。1944年5月1日至25日,在陜甘寧邊區(qū)工廠廠長(zhǎng)暨職工代表大會(huì)上,邊區(qū)政府向陳振夏頒發(fā)了“特等工業(yè)模范工作者”獎(jiǎng)狀,以資鼓勵(lì)。5月22日,毛澤東親筆為陳振夏題詞:“埋頭苦干”,這是對(duì)延長(zhǎng)石油人最高的褒獎(jiǎng)。同年7月底的延安《解放日?qǐng)?bào)》上,發(fā)表了陳振夏先進(jìn)事跡的專題報(bào)道,贊揚(yáng)他“對(duì)本身業(yè)務(wù)非常盡職,終日不倦”,“把專門的技能與群眾的偉大創(chuàng)造結(jié)合起來,從來不以技能自私,從來沒有門戶之見”。當(dāng)年12月下旬,陜甘寧邊區(qū)勞動(dòng)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huì)隆重開幕,評(píng)選出新一屆特等勞動(dòng)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陳振夏榜上有名,再次被授予“特等工業(yè)模范工作者”稱號(hào)。頒獎(jiǎng)會(huì)上,邊區(qū)政府領(lǐng)導(dǎo)把毛澤東題寫的“向戰(zhàn)斗在生產(chǎn)第一線的勞動(dòng)英雄致敬”的獎(jiǎng)狀發(fā)給了他,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題詞表彰陳振夏。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在大會(huì)上作《必須學(xué)會(huì)做經(jīng)濟(jì)工作》的報(bào)告,肯定了陳振夏等英模“有許多的長(zhǎng)處,有很大的功勞”、起了“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1945年2月,陳振夏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他是在延長(zhǎng)油礦成長(zhǎng)起來的勞動(dòng)模范、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他走到哪里,就把共產(chǎn)黨員的優(yōu)秀品質(zhì)帶到哪里,把延長(zhǎng)石油人的埋頭苦干作風(fēng)傳到哪里。新中國(guó)成立后,陳振夏帶病先后在河北石家莊農(nóng)機(jī)廠、石家莊動(dòng)力廠和保定機(jī)床廠任副廠長(zhǎng)、廠長(zhǎng),在轉(zhuǎn)任廠長(zhǎng)的近20年中,一直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兼辦公室里,組織上幾次要給他調(diào)整工資級(jí)別,他都主動(dòng)放棄。1972年,退休后回到家。他繼續(xù)保持延安時(shí)期的艱苦奮斗精神。組織給他300元安家費(fèi),他沒拿;給他新建房屋,他不要,提出要和群眾一樣分配公房,幾次請(qǐng)他搬進(jìn)新樓居住,他都婉言謝絕。他說:“我出身鄉(xiāng)村,在延安住窯洞,現(xiàn)在住這樣的房子已不錯(cuò)了,和群眾相比,我的住房還算是好的。”縣里照顧他去醫(yī)院看病可用小汽車接送,但作為老石油人,他寧要老伴叫三輪車,也不讓國(guó)家為他耗費(fèi)汽油。1973年,他將變賣兩間住房所得650元全部交了黨費(fèi),還把鄉(xiāng)下老家3間房屋送給生產(chǎn)隊(duì)開店。“不徇私情不特殊”、“共產(chǎn)黨員姓‘公’不姓‘私’”,這是陳振夏經(jīng)常講的兩句話,也是他的處事準(zhǔn)則。他退休后,參加組織生活風(fēng)雨無阻,有時(shí)臥床不起,也一定要老伴代他請(qǐng)假。陳振夏把畢生精力都用在了開礦辦廠為“公家”了,作為老廠長(zhǎng),他的聰明才智毋庸置疑是用在了“刀刃上”,作為老黨員,他的聰明才智毫無疑問也是用對(duì)了地方。他,剛骨所在,夫復(fù)何求;不虛此生,無怨無悔!他用一生忠實(shí)地踐行了延安精神,永遠(yuǎn)是我們學(xué)習(xí)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