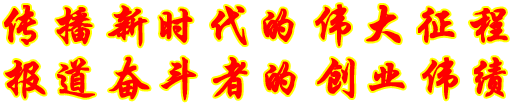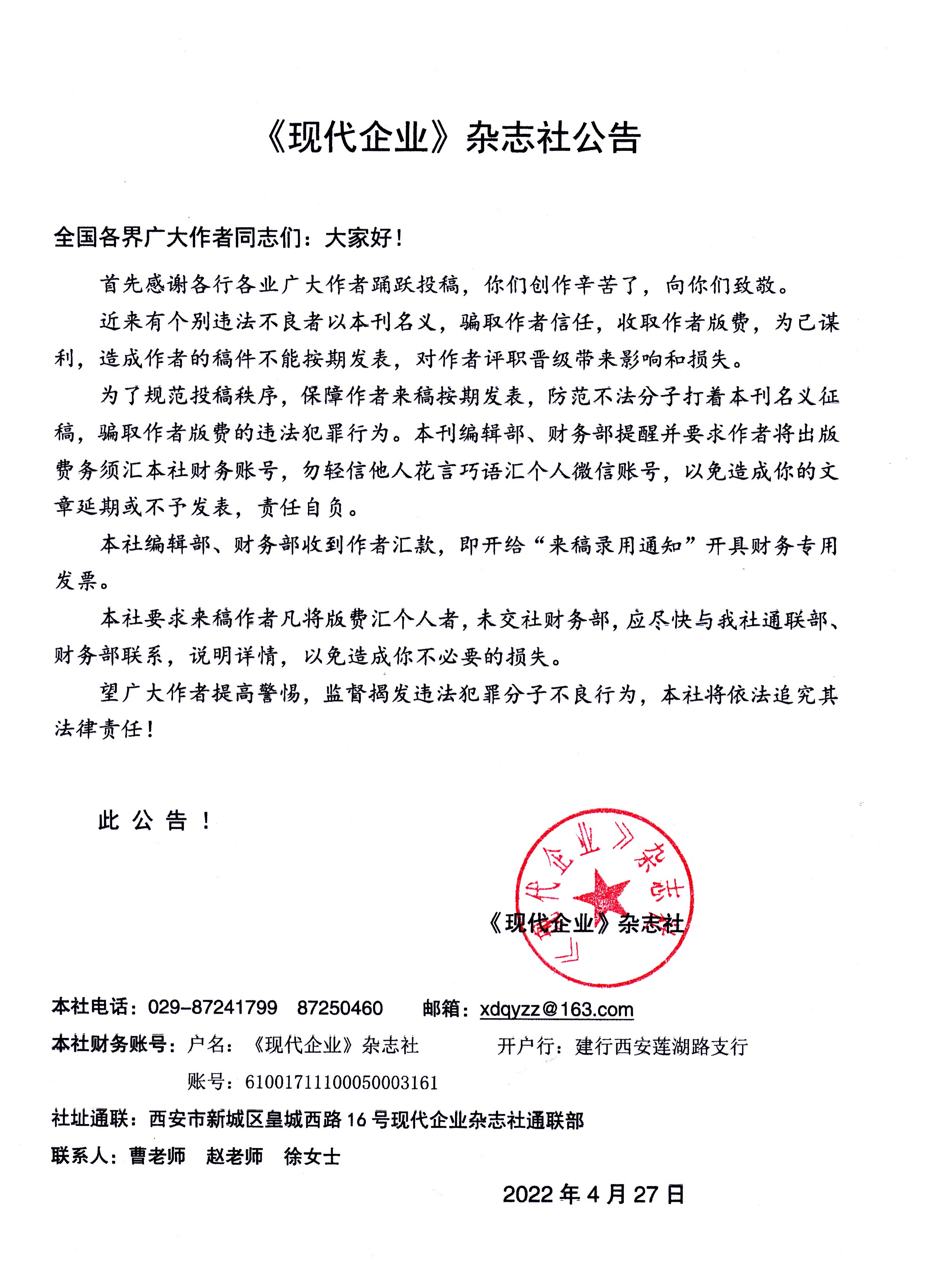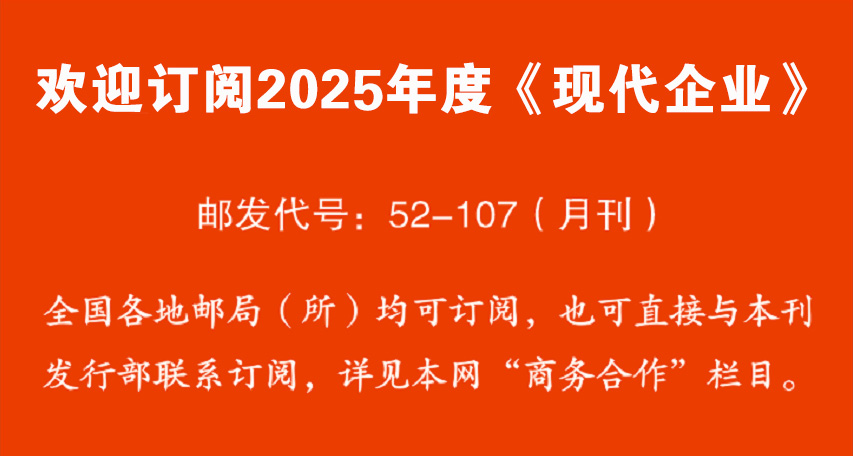一個優秀的記者要善于通過采訪集聚各種正能量,并最終把正能量由小溪匯聚成江河

1.83米的身高,壯碩得像頭大熊,跟他握手時,多數人會覺得自己能被他裝進去。他眉目慈祥,愛笑,高顴骨上的眼睛瞇起來很聚光。
他是湯計,一個做了30多年記者的新聞“老炮兒”。
湯計今年61歲了,一年前,他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編委的位置上退了休。而退休前的2015年,他跟蹤報道了9年的“呼格案”塵埃落定,更為他贏得了一個記者職業生涯中幾近所有的榮譽:新華社榮記個人一等功、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全國先進工作者、CCTV201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為基金化緣
退了休的湯計,卻一點沒閑著。
每天還是有人找“湯記者”,但他基本上只是給一些建議或意見。
他寫的《職責與真相》已出版,內容是湯計新聞從業感悟。
他是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平時還在一些大學和媒體講課。
但目前最牽扯他精力,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張羅他的基金。
為新聞人“化緣”
9月27日,“湯計人道傳播基金”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設立。湯計說,他這個基金是專門給新聞人設的,也是當下中國唯一的用于新聞從業人員的慈善項目,“我想為記者建造一座豐碑,讓杰出的記者永遠留在豐碑上”。
湯計拿出了退休前所獲的各種獎勵10萬元,聯合了四家認同他理念的企業,一開始籌了總共200萬。這是基金設立的必備條件。
但湯計覺得不夠,基金成立后,他的退休生活也由每天閱讀變成了分分鐘在“化緣”。
今年的國慶節,湯計都在不停“化緣”,他多年職業生涯積累的公信力讓湯計人道傳播基金一個小長假下來收獲捐款10萬元。
除了化緣,湯計現在緊鑼密鼓地在籌備首屆“湯計博愛新聞獎”的評審。
這個獎主要用于“褒獎和傳播那些為人道公益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新聞作品以及新聞從業人員;救助因采寫報道等因公負傷或陷入困境的記者或媒體從業人員。”
設計呼格的新墓地
去年中元節,湯計提前兩天邀請了所有對呼格案有貢獻的人,去呼格新遷的墓地憑吊獻花。
離呼和浩特市區30公里遠的和林格爾縣安佑生態園內的寶珠山半山腰,呼格的墓在園區路邊很顯眼的位置,墓志銘上寫著:其生也短,其命也悲。
呼格案的整個來龍去脈被湯計刻在墓碑背后的不銹鋼裝飾板上,他覺得這個不銹鋼板和大理石質地的藝術墓地設計得很成功,像滴眼淚也像個問號,予法律敬畏,還生命尊嚴,昭示著真理和正義永遠不會埋沒。
2014年12月15日,冤死18年的呼格吉勒圖終于被法院宣告無罪,那一刻的湯計淚流滿面。
湯計說“人太高興了不是笑而是哭”,之后他雙手合十的動作被在場的媒體拍下來,成了經典形象。
現在,又過去了近3年,再敘述這段歷史,湯計少了當年的吶喊與感慨,多了掩卷落定后的淡定與思索。
湯計認為呼格案的徹底平反昭雪,從根本上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決定的推出,沒有這個,呼格冤案或許會繼續拖延下去。
“呼格案真正改變的是刑訊逼供”,現在,湯計在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長赫峰閑聊時,還會討論到這個案件在法律程序公正性上的推動。
赫峰認為,現在“以審判為中心”一改過去“以偵破為主”的制度,法律界已經有了共識,即法律剝奪個體生命的過程越復雜,也就意味著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張,更意味著冤假錯案的幾率被降低到最低。
重新出發
什么是正確的新聞觀?湯計說,“好記者必須是好人,要有慈悲心和正義感。”
他還記得內蒙古農牧廳農機公司退下來的三十多名老職工送來錦旗的那天,其中一位老人進門就跪下來,他說我代表這些老人謝謝你幫我們要回了200萬元的社保金。
“老百姓支援邊疆、奉獻青春,因為政府失信于民,讓這些下崗老職工在國有公司改制中失去了經濟來源,成了兒女和親友面前的乞食者。如果我們的政府認真工作,就不會出這樣的事。但是有些人只想當官不想擔責,最后還要我這個小記者扛著輿論監督的旗才給解決了,老百姓還要給你下跪。”湯計嘴唇扭動,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作為一名老記者,湯計也感慨過——“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他做了微信公號“湯計典頻”,并加入了騰訊的“芒種計劃”,“湯計典頻”作為首期進駐的公眾號,湯計也嘗到了不少“甜頭”。
“挺意外的,真沒想到閱讀量增長會這么快!”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他在該平臺上的所有文章閱讀量達到700多萬,5月1日,當日文章的原創補貼收入已經破萬。
他組建了公號運營團隊,隊員有內蒙古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的研究生,還有媒體的編輯與記者。
湯計說,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新聞多,但雜音也多。“當時,我就在想,如果我們這些經過良好新聞職業培養的新聞人能參與其中,這會使這塊新陣地的正能量聲音放大,好新聞增多。”